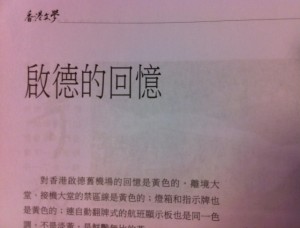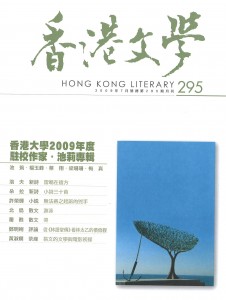對香港啟德舊機場的回憶是黃色的。離境大堂、接機大堂的禁區綫是黃色的;燈箱和指示牌也是黃色的;連自動翻牌式的航班顯示板也是同一色調。不是淡黃,是鮮豔無比的黃。
不是令人舒服的顔色,是警告、提醒的顔色,和機場的實用性很吻合,但對於這裡曾發生過的許許多多悲歡離合,未免過於喧嘩。
啟德離境大堂的白色天花不是很高,由一個個方塊組成,每隔幾個方塊便裝嵌了白色的光管,光管很白,把人的臉照得清光。乘客進入禁區的地方,兩邊是白色的圍板,中間是另一塊圍板凹了入去,圍板上用紅字寫有「禁區」「離境」的字眼,很有阻嚇作用,令到送機和被送的人,心情格外深重,因爲只要被送的人走向三塊圍板的中心點,就會從此消失在送機的親朋視線外。沒有背影,沒有目送,沒有回頭,沒有多一眼的想念。
第一次一個人去歐洲讀書,就是在這裡和家人說再見的。身處禁區前不遠處,背對著禁區,時間一分一秒過去,爸爸雖然百般不捨,但嘴在催,要我起行,我知道是真的要轉身離開了,但一轉身,就是走向三塊圍板的禁區,一踏入那裏,一個閃身,就是一個人了。那是我經歷過的最艱難的一個轉身。
也是在這個離境大堂,送過不少人離開,有因爲九七而選擇移民的朋友、有出國讀書的朋友和親人……有的分離是刻骨銘心的。記得白光滲透的大堂,零散竪立了不少方形柱子,我和朋友選了在一角偏僻的柱子後靜靜談話,柱子前人來人往,航班顯示牌不斷翻滾航班號碼和訊息,發出「噠噠噠」的聲音。 是時間走了,不得不走了,朋友慢慢走向三塊圍板的禁區,我目不轉睛地盯著,就在消失前,他頭也不囘,突然把頭上的帽子舉起,揮揮,消失了。我找到我們原來站在後面談話的那根柱子依著,透透氣,回過神來。
舊的東西令人有所依傍,就像這些柱子。現在的機場設計先進,很難再找到柱子了,雖然環境寬敞舒適了,但總感到有點逃無可逃。
啟德的離境大堂不大,但相比其接機大堂,已是十分寬敞,啟德接機大堂只有一個接機處,兩邊用金屬欄杆圍出一條寬闊的長通道給抵港人士使用,後面是幾扇自動門,推送出一個又一個抵埗的人。通道是慢慢向下傾斜的,兩旁站滿了引頸企盼的接機的人。下機的人一走出自動門邁向通道,難免有點緊張,因爲兩旁有那麽多人注視,就如明星走過紅地毯受到萬衆矚目一樣。
舊時去啟德接機,覺得很好玩,因爲只有一個接機處,當有新的航班抵港,同一時間會有很多人一起步出閘門,你要很快地從人群中辨認要接機的人,並且要比爸爸和兄弟姊妹還要快,成爲第一個認到要接機的人,然後仗著個子小,敏捷地穿過欄杆中間的空處,跑到通道上和要接機的人相認。
那時家裏清貧,去舊機場都是因爲接機,不是因爲要出遠門。因爲住港島,去機場要搭隧道巴士,初時跟父親去機場,不知哪裏下車,父親說到了,就跟著下車,後來去機場多了,知道見到漢寳酒樓的牌子就下車。落車處附近有條行人隧道,走過隧道,就可到達接機大堂。機場所在的九龍城多美食,我喜歡在隧道口附近的餅家買件餅,或買串串燒之類,才施施然和父親一起走向機場。
接完機,再走過行人隧道去到另一邊,那裏有一列巴士站,巴士站旁就是鐵欄圍起的機場,可以見到飛機在停機坪移動和升降,耳畔傳來隆隆的飛機聲,震耳欲聾。夏天時烈日當空,加上飛機的聲音,令人很焦躁,這時最盼望是快點搭上有冷氣的巴士回家。
後來,終於自己可以搭飛機了,才真正領會到啟德機場的獨一無二,一條跑道深入維多利亞港,跑道的盡頭就是民居和山頭,飛機降落時,低飛而過,十分貼近民居,一旦發生意外,後果堪虞,啟德因此被視爲全球最危險的機場之一。慶幸啟德歷史上從未發生過嚴重飛機意外。那時坐飛機回港,並不覺得危險,倒是常懷期盼的心情 – 終於可以回家了,真好。期盼之外,還有興奮,尤其是晚間降落機場,夜幕低垂,萬家燈火,飛機俯向九龍城,在城上低飛,從飛機外望,有時甚至可以看到屋内人的起居生活,一個窗口連著一個窗口,每個窗口内都有人在活動,彷似走入天上人間。
1998年啟德關閉,天上再沒有人間。
啟德舊機場關閉時,我剛好是一名電視台記者,為了拍一個有關舊機場的特輯,和兩位攝影師幾乎走遍九龍城每個角落,只為捕捉飛機在頭頂、屋頂、天台掠過的奇景,當飛機由這邊屋飛到那邊屋,橫過一街之隔時,尤其感震撼。我們甚至上到九龍城一戶人家的天台拍攝,看飛機越過晾衣架和雜亂的天綫低飛而過,飛機似在伸手觸及的地方一飛而過,那震撼是更大了。
拍完啟德不久,啟德就關閉了,我也離開記者這一行了。
啟德消失後,香港機場從此融入全球化的大洪流,不斷和其他機場比拼,比拼機場跑道的多寡,比拼每分鐘起降的飛機數量,比拼誰提供的服務最好,比拼誰是最受歡迎國際機場……傳奇不是這個世界需要的。
啟德沒有了,香港的傳奇也消失了。
令人更懷念啟德。